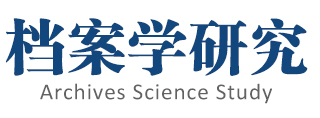以朱熹为例,对南宋书院档案作出初步探讨,对朱熹所遗存的文书、学规、教材、题刻四类档案予以详细录述。
Abstract:
南宋是中国书院蓬勃兴起、活力四射的黄金时期。书院兴盛的源头活水,是朱熹自兴复白鹿洞书院时注入的。白鹿洞书院一扫北宋书院的陈腐之气,开启了书院崇教尚学、建章立制、置田延师的新风气,为明清书院的进一步繁盛铺设了基石。朱熹之成为书院的精神象征,不仅在于他借助书院传播程朱理学的成就之大,也在于他创建、兴修、讲学、题词的书院数量之多、影响之巨。朱熹不仅赋予书院以无形的精神文化,也赋予书院以有形的文献资料。南宋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卷一《慈湖书院记》云:“睢阳、白鹿为称首,若周、程、朱、吕治教之地,文献尤盛。”书院档案,则是书院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以朱熹为中心,对南宋书院档案加以探讨。
朱熹所遗存书院档案,因出于本人之“口舌手笔”,所以其“价值之高实驾于后世所修史传之上”。①这些档案散见于文集、地方志、书院记、碑刻之中,分为文书、学规、教材、题刻若干类型。
与北宋相比,南宋书院行政文书明显增多,表明书院在南宋时期已显现官学化的端倪。书院文书档案涉及书院创建、兴复、行政、经费、礼仪诸方面。朱熹有关书院文书档案,按照《朱熹文集》文种分类方法,分为奏状、公移、祝文等。
1.奏南宋时期,朝廷常以敕额、赐御书的方式奖倡书院,尊崇理学。“有屋庐而无敕额,有生徒而无赐书,流俗所轻,废坏无日。”②南宋书院申请敕额、赐御书的奏章,大多收集在志书与文集中,如朱熹《乞赐白鹿洞书院敕额》、《辛丑延和奏扎》。
据王懋竑《朱子年谱》:淳熙八年,朱熹离任南康,奏本职四事,其中第四件事就是“降敕赐白鹿洞书院额及颁赐太上皇帝御书九经注疏印本等书。”在《乞赐白鹿洞书院敕额》中,朱熹申请曰:“欲望圣明俯赐鉴察,追述太宗皇帝、真宗皇帝圣神遗意,特降敕命,仍旧以白鹿洞书院为额,仍诏国子监、仰摹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大上皇帝御书石经及印板九经注疏、《论语》、《孟子》等书,给赐本洞奉守看读,于以褒广前列,光阐儒风,非独愚臣学子之幸,实天下万世之幸。”③但“未蒙施行”。同年十一月,召对延和殿,再次奏请敕额御书,是谓《辛丑延和奏扎》。孝宗应允,诏国子监印造《九经注疏》、《论》、《孟》等书,赐予白鹿洞书院。
2.状朱熹一面筹措兴复书院之事,一面拟写《申修白鹿洞书院状》呈报尚书。在《申修白鹿洞书院状》中,朱熹批评说:“老佛之居以百十数,中间虽有废坏,今日鲜不修葺”,与此相反,白鹿洞“乃前贤旧隐儒学精舍,……惠养一方之士,德意甚厚。”但累年“废坏不修”,他认为:“书院工役虽小,然其名额具载国典。”同时请求尚书省及尚书礼部降下钧旨,按照“太宗皇帝在太平兴国年中节次指挥,行下照会,庶几官吏有所遵守,久远不至湮没”。“朝廷倘欲复修废宫以阐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则熹虽不肖,请得充备洞主之员,将与一、二学徒读书、讲道于其间。”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定义“公移”为“诸司相移之词”,上、下、平级之间均能通用。“唐有状、辞、牒、关、刺、移等,宋有札、申状、公牒,明有照会、札付、案验、帖、故牒、咨呈、案呈、呈、牒呈、申、咨、牒、关、揭帖等,因“其名不一,故以‘公移’括之”。④朱熹兴修书院须下发公文时,常使用榜、牒两类文种。
1.榜榜是古代官府发布指示,晓谕官民的一种布告文书。朱熹知南康军期间,为兴复白鹿洞书院,发布了《知南康军榜》、《洞学榜》等。
淳熙六年,朱熹张贴《知南康军榜》,询究白鹿洞书院遗迹,榜曰:“右牒教授杨迪功、司户毛迪功,请详逐项事理,广行询究,取见指实,逐一仔细条具回申,以凭稽考,别行措置。”“仍榜客位遍呈寄居过往贤士大夫,恐有得知本军上件事迹详细,切幸特赐开谕及榜市曹,仰居民知悉,如有得知上件事迹详细之人,仰仔细具状,不拘早晚,赴军衙门申说,切待并行审实措置施行。”⑤
淳熙八年,白鹿洞书院建成后,朱熹为防止人毁坏、骚扰,发布《洞学榜》,榜云:“窃虑向后诸色等人不知上件事理,或有毁坏,以致偷盗文籍,侵占田土,及过往之人妄有骚扰,事属不便,须至晓示者。右出榜白鹿洞书院张挂,各请悉知。”⑥
2.牒 “牒者,用之官府也。”宋代,牒不仅有上行、平行之分,而且下行牒脱颖而出。《白鹿洞牒》、《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就是南宋的一种下行牒。
《白鹿洞牒》是朱熹向南康乡绅征询兴建白鹿洞书院的意见而发的。他从《国朝会要》、本军图经记文石刻获悉,白鹿洞书院曾“学者大集”,“学徒尝数十百人”,知南康军之初,“亲到其处,观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他说:白鹿洞书院“废坏无不兴葺”,“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惧”。因此,他认为“长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责”,“庐山白鹿洞书院合行修立”。⑦
绍熙五年,朱熹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他对“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的书院颓废之风甚为惋惜,决心“复置岳麓书院”。因此拟写《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牒教授及贴书院”。牒提出:“革流弊以还旧规”,“为有志之士不远千里求师取友至于是邦者无所栖泊以为优游肄业之地。”⑧
祝文是古代祭祀神鬼或祖先的文辞。刘师培《文章学史序》说:“以人告神,则为祝文。”《礼记·文王世子》曰“凡始立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三国魏正始之后,规定入学行祭礼,沿及南宋书院,释奠之风尤盛,如白鹿洞祀李渤,石鼓祀李宽,睢阳祀戚同文,岳麓“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以白鹿洞书院为例,淳熙七年三月十八日,书院释菜开讲,朱熹“率宾佐合师生,恭修释菜之礼”,⑨撰《白鹿洞成告先圣文》、《白鹿洞成告先师文》,以告于先圣至圣文宣王,先师兖国公、邹国公。
南宋时期,书院逐步制度化,订立较为完备的学规,是书院制度化的主要标志。学规,系包括宋儒所厘定的重要教条教法和学校书院的规则。⑩清邹召南《丰州集稿·碑记》说出了“养士之规”的重要性:“有造士之地,不可无养士之规。……一切章程未及厘定。上之,不能为国家宣扬尊经稽古之巨典;下之,不能以诸生考究明体达用之实功。”
宋绍兴二十六年,朱熹与傅自得登游九日山时,与傅自得创设九日山书院,并集儒家经典成语,制订“教条”:“一为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二为学之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三为修身三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为处事之要: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五为接物之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淳熙七年,朱熹深化九日山书院教条,揭示“圣贤教人大旨,学者立身之要”,形成《白鹿洞书院揭示》。该揭示也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学规》、《白鹿洞书院教规》。绍熙五年,朱熹振兴岳麓书院,将《白鹿洞书院教条》颁于该书院,史称《朱子教条》。
淳佑元年,理宗视太学,亲书朱熹《白鹿洞学规》以赐,于是学规为各书院、各学校所取法,已随程朱理学而广为流传。如朱熹弟子叶武子“调郴州教授,一以白鹿洞学规为诸生准绳”。朱熹再传弟子吴昌裔任眉州教授,“揭白鹿洞学规,仿潭州释奠仪簿。”唐璘“调瑞州学教授,用白鹿洞教法,崇礼让,后文艺”。
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说:“至若唐之韩、柳,宋之程、朱、张、吕,凡其所与知旧、门人答问之言,率多本乎进修之实。”南宋时期,学校教材较为零散,不成系统,一些书院唯“朱”是真,将朱熹“与知旧、门人答问之言”刻为教材,供生徒研读。这些教材又可划分为讲义、语录和经典课本。
“既有讲堂则有讲义。两人对面谈话有语录,多人群集一堂则有讲义。”讲义,有“预先撰拟”的,如清吴曾祺《文体刍言》说:“人君于听政之暇,使词臣入伺经筵分日进讲,其所讲之书恐不能详尽,皆预先撰拟,号之为讲义也”;也有讲说之后笔录的,如朱熹《跋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义后》说:“熹犹惧其久而或忘之也,复请子静笔之于简.而受藏之。”
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初步修复,朱熹率军县官吏、书院师生赴书院,祭祀先师先圣,行开学礼,升堂讲说《中庸首章》,《中庸首章》后被刊刻成讲义,对后学影响颇为深远。此外,朱熹其他的讲义,如《中庸首章》、《大学或问》、《白鹿洞讲堂策问》,也被后人收录到《朱子文集》、《白鹿洞书院志》中。
另据王懋竑《朱子年谱》,绍熙五年十一月,朱熹至玉山,“邑宰司马迈请为诸生讲说,先生辞不获,乃就县庠宾位,因学者所请问,而发明道要,闻者兴起。迈刻讲义一篇,以传于世。”此即《玉山讲义》。
《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是朱熹“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的记录。朱熹弟子黄干《池州刊朱子语录后序》云:“晦庵朱先生所与门人问答,门人退而私窃记之。先生没,其书始出。”
书院经典教材《四书集注》,集诸儒之大成,是朱熹沉潜反复,用力最勤的著作。据王懋竑《朱子年谱》考证,《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完成于淳熙四年,《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改定于淳熙十六年。宋嘉定五年,《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列入官学,作为法定教科书。
据统计,朱熹一生与67所书院有关,其中亲自创建的有4所,修复的有3所,读书的有6所,讲学的有20所,曾经讲学而后人创建的21所,撰记题诗的7所,题词写匾的6所。
碑石是南宋书院档案的重要载体之一,龚自珍说:“国之大政也,史之大支也。或纪于金,或纪于石。石在天地之间,寿非金匹也,其材巨形丰,其徒也难,则寿俟于金者有之,古人所以舍金而刻石也。”关于题名石刻的档案价值,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说:题咏题名“往往可补志乘之阙,若整理而汇录之,皆治史者考据之资也”。根据方志记载,朱熹题名石刻主要有:
福建: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十四载:浣溪书院,淳熙二年 “朱文公书匾”。螺峰书院“‘文昌阁’三字,朱文公所书也”。义宁书院,“宋淳熙元年刘爚建,以为师友讲学之所,朱熹题匾”。清乾隆《晋江县志·书院》载:小山丛竹书院“地处高埠,其气独温,温陵之名,实肇于此。朱文公种竹建亭,讲学其中,匾为朱子手书,镌于石。”
江西:据《庐山志》、《星子县志》、《白鹿洞志》,白鹿洞书院现存朱熹题刻四则:“敕白鹿洞书院”、“枕流”刻于枕流桥下流芳涧中石壁及砥石上;“白鹿洞”、“自洁”刻于桥头蹲鹿坡之左。
湖南:乾道三年,朱熹手书“忠孝廉节”于岳麓书院讲堂,书院奉之为校训。
“纪事刻石者,纪当时之事实,刻石以表章之也。”朱熹纪事石刻,数量稀少。传世者,乃淳熙十四年四月,朱熹应衡州知州宋若水之请,为石鼓书院撰《衡州石鼓书院记》。书院立石刻碑以传。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