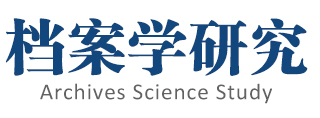自有文明史以来,中国就设有专门机构或人员进行天象观测与研究,并形成天文档案。它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天文观测记录及其所形成的星图星经等;二是历书档案。历代绵延不辍的天学机构既是天文档案的形成者又是主要管理者,其良好的保管制度和各朝天文史志的编研为我们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天文档案遗存,它可分为两大类:直接遗存与间接遗存。
Abstract:
From civilization, china had special institution and personnel to observe and research astronomical phenomena, and form astronomical archives. It has two species, first is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 records and its star map; second is ephemeris archive. Past dynasties’ continuous astronomical institution was not only fabricant of astronomical archives, but also primary supervisor, its nice storage system and past dynasties astronomical history archive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leaved behind large number of astronomical archives for us, including direct remains and indirect remains.
天文学是一门对观察记录具有很强依据性的学科,这些观测记录前后相因,不断积累,为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些积存起来的天象记录等,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文档案。早期的天文档案主要有两类:一是天文观测记录及据其所形成的星图星经等;二是历书档案。
天文观测活动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原始先人们对充满神秘且对人类生活关系巨大的天空经常仰望、观察。一旦他们掌握了记录这些天象的工具,最初的天象记录就产生了。事实上,最早的图象记录的产生要早于文字的产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面有带芒的太阳、月牙和星星等。①其他遗址中也有此类发现。
自有文明史以来,中国就设有专门机构或人员进行观测和研究,并由此而形成了天文档案。学者们根据现今所掌握的材料断言:“自有文字以后的天象均有记录。”②而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字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字。以此和大河村彩陶等出土图象等相对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古代天文档案记录最迟出现于新石器时代。
历法档案的产生要晚于天象记录档案,因为历法是人们认识天象到达一定程度后的产物。据现有材料看,中国历法档案最迟产生于夏代,《夏小正》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依据(在夏代之前,文献中就有有关历法的记载,但没有有力的证据加以证实)。人们通常认为,《夏小正》成书于战国,但通过历来考证,认为内存夏代的资料,与传说相符。作为一种物候历,它显然是早期历法的代表,同时它还记录了一些天象。
历法与农业生产关系甚为密切。而国家政权负有领导农业生产之职责,因此,制订和颁布历法就成为中央政府的一种职责。所颁布的历法原本要郑重地保存起来,这就形成了历法档案。关于历法档案的产生过程,历来都有较严密的制度,先秦更是这种制度的滥觞期。通过甲骨档案,我们可了解商代的历法档案。在我们现今所发现的甲骨档案中,有一片记载的是殷代的“月令”,内容是一月和二月的干支表,它应是整部殷代年历的一部分,这部殷代历法档案的其他部分可能已散失。
由于天文学与农业生产及古人的政治生活关系密切,因此,它极受先人重视。有史料记载,历代皆设有专门机构或人员进行观测与研究,并由此而形成了天文档案。根据文献记载,从三皇五帝时期开始,就设有专掌天文之人员。远古的重、黎、羲和,春秋战国的甘德、石申夫,《周礼》记载中的保障氏、冯相氏等,皆是此类人员。他们通过长期观测、积累,常常形成大量的天文观测档案。如甘德、石申夫根据各自所掌握的大量的天文档案记录,分别著成《天文星占》八卷、《天文》八卷,合称《甘石星经》。据专家们研究,这部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所需的材料,应是数百年长期观测的档案记录之汇总,绝非少量短期记录所能胜任。③这一事实有力地证实了当时确有长期观测、记录、保存天文档案的工作。而《周礼》的记载,更是给我们提供了较详细的情况。
事实上,定期进行天文观测并加以记录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传统,即所谓“礼”。如《左传》载:“僖公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今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以备故也。”意思是:僖公五年春季的第一个月(十二月)辛亥日(即这个月的第一天),太阳达到最南点。鲁僖公下令在宗庙中宣告新月即将出现后,便登观象台去观察日影,而天文官们则按照惯例作下记录。在每个分日和每个至日,在春夏秋冬开始的时节,都必须记录下云雾的样子,以便对即将到来的变化作出预测和准备。
从中国古代天文机构的演变中可以看出,虽然古代天文机构名称繁多,隶属关系不一,职能屡有变动,但基本上没有跨出观测天象、编制历法及进行星占活动的范围,因此很好地保持着三千年一脉相承的传统。古代天文档案的形成与管理同天文机构的职能是密切相关的。以唐代为例,我们便可知中国古代天文档案形成与管理之大概。
唐代,中央政府的天文机构趋于完善,天文观测、历法档案的形成与管理也更为专门化。唐设司天台(或称太史局等),专掌天文星历之事,成为独立的国家天文气象机构。司天台除设有监、少监、丞、主簿等外,主要有正、副正、保章正、监候、司历、灵台郎、挈壶正、司辰等。这些官员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都加上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等五官为名。五官正各一人,副正各一人,掌四时及其四方变异,为特殊星象记录档案之形成者,其记录或预测文件要上奏,保存于宫廷秘阁。五官保章正各二人,五官监候各三人,五官司历各三人,掌历法及测影,为历法档案的形成者。历法文件亦要上奏,正本保存于内廷。五官灵台郎掌观测天文变化,为观测记录档案的形成者。
此外,司天台的部分天文档案亦要报送史馆,以供修史之用,报送天文档案材料包括“天文祥异”④和气象材料等。《旧唐书·职官志》载:司天台“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予焉。每季录所见灾祥,送门下中书省,入起居注,岁终总录,封送史馆”。因此,史馆亦保存有天文档案。
所谓古代天文档案直接遗存是指以天文档案原件或原件汇编形式遗留下来的古代天文档案材料。
(一)以原件形式遗留下来的中国古代天文档案。
出土文物中有一部分是珍贵的天文档案。它们大都散存于其他出土文物之中,存有数量不一,而致使难以准确统计。这些出土的天文档案能够被保存下来并为今人破土重现,实属不易,因而为当今人们了解与研究古代天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例如: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当初是作为墓主陪葬品被深深埋藏于地下的,而一旦重见天日,则为研究先秦时期行星运动知识和行星占学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敦煌卷子是保存至今的中国古代宝贵文献,其中有不少与天文档案有关,著名的《敦煌星图》就是一例。至于殷墟甲骨文中的天文记载,则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久远的天文档案。
出土文物从埋藏到被发掘出来,中间人为的因素已降到极小,所以出土文物中的天文档案是研究古代中国天学的可靠资料。
现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天文档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钦天监的档案,只有九卷共35件;二是钦天监进呈皇帝的题本,约有2381多件,这些向皇帝报告天文气象和进时宪书题本,当时收藏在内阁大库,以后一直留存至今。现将其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时宪书俗称“历书”。每年二月初一日,钦天监以来岁时宪书式本进呈皇帝阅览。皇帝阅准后便印制正式历书。于“孟冬之朔”将来年时宪书进呈皇帝:其中善录满、汉御览《时宪书》各一本,刷印满、汉、蒙古文字《时宪书》各一本,满、汉文字《七政时宪书》各一本,都是黄绫封面。同时进皇太后、太后刷印满、汉、蒙古文字《时宪书》各一本,刷印满、汉文字《七政时宪书》各一本。然后颁发给亲王、贝勒、文武各臣。颁给亲王的《时宪书》,用红绫面,颁给大臣《时宪书》用黄纸面。十月初一日,王公大臣皆穿朝服在紫禁城午门外行礼跪领。现存清代《时宪书》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四百余本。
观测天文气象的文书。凡元日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日,各以交节之时验风、验雷,三日后具题报告皇帝,并附此一时期的天象图(文图皆满汉文合璧),这方面的题本较多。钦天监观测日、月食的题本也很多,主要记载有:钦天监某臣遵御制《数理精蕴》等历算书籍推演得某日、某时,京师以及各地的日、月食初亏时分、食甚、复原时刻,还有应采取的救护措施等内容。这些有关观测天文气象的文书大约有2100余件。
选择时候和占卜方面的文书。清代凡遇有应行典礼,考其宜忌,都由钦天监选择时候。凡修建坛庙、山陵、宫殿、城垣等重大工程,也要由钦天监选择时日开工,结果形成了大量的选择时候的文书。
除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外,其他省、市档案馆中也收藏有少量的天文档案。如:内蒙古自治区四王子旗档案馆保存的四王子旗历史档案联合全宗(全宗号—11):该全宗主要是历书;云南省江城县档案馆保存的彝文档案汇集(档案号—1):记载了该县的天文、历法、药书等文书,等等。
(二)古代天文档案汇编。
在前面介绍中国古代天文档案的直接遗存中,清以前主要是出土的天文档案。但这些出土的天文档案数量与当时实际形成的天文档案数量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清以前的中国古代天文记录主要是以什么方式留存下来的呢?是档案汇编。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常常有意识地将天文档案中的天文观测记录、星表等汇编成册,保存下来。这种直接遗存具有条理化的优势,并能够广泛地传播开来。
古代著名的天文档案汇编有: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天文图像档案汇编《天文气象杂占》帛书、集唐以前古天文星占记录之大全的《开元占经》等。古代天文档案汇编在中国古代天文档案遗存中占有重要比例,远不止以上所举各例。而今人针对古代天文档案所做的汇编工作也不落后于古人,其著名的天文档案汇编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合编的《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1997年),以及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1988年)、《我国古代航海天文资料汇编》(1977年)等。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几千年来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天文档案资料,引起各国天文学家的关注。就文献数量来说,天文学可与数学并列,仅次于农学和医学,是构成中国古代最发达的四门自然科学之一。
中国古代对天象的原始观测记录除了以上所述之直接遗存外,还有经过改编和加工的第二手、第三手资料,作为中国古代天文档案的间接遗存,得到了较为系统的保存。现今所见的古代天文档案间接遗存大致来源于三个方面:
由官方进行系统保存而留存至今的天学文献占了天文档案间接遗存的大部分。这部分文献首推“天学三志”,即历代官史中的“天文志”、“律历志”和“五行志”。其中“天文志”记载当朝主要天象变化及对应的占辞和事验,“律历志”则记载了该朝几部主要历法的原理和基本数据。现在关于古代的历法资料和大部分天象记录主要求之于“天学三志”。另外,一些古代官方修定的大型类书中也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天学资料。如:唐初编撰的《艺文类聚》,以“天”部为第一,其“岁时”、“符命”、“祥瑞”和“灾异”各部也与天学有关。宋代王应麟辑《玉海》分为二十一门,以“天文”、“律历”开头。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分六编三十二典,第一“历象编”又分为“乾象、岁功、庶征、历法”四典。
地方志是记述特定区域、特定时空内一个方面或各个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简称方志。方,地方、方域;志,记也。“永志不忘”、“日志”即取此意。
我国有2000多年的修志传统。地方志是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资料著述。地方志书包含有各种社会科学著作, 乃至自然科学著作所需的资料。也就是说,地方志资料不仅对社会科学研究有重要作用,而且对自然科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就辑录了大量古代地方志中保存的有关太阳黑子、极光、陨石、日食、月食、月掩行星、彗星、流星、流星雨、新星和超新星等天象记录。这些记录散存于地方志的自然现象或灵异现象等之中,记录语言有较强的文学性,不够严谨科学,有的仅写一小段,有的仅存一句话。例如:有关太阳黑子的记录明太祖洪武元年自正月至十二月(1368年1月20日~1369年2月6日)“日中有黑子”⑤;有关极光的记录清世祖顺治五年十二月三十日(1648年)“时一更,天垂白气如练,四布直披约数十余道,寒光下射,悸人心目。”⑥虽然地方志中保存的天象记录过于零散,记录内容不够详细和科学,但是由于它们数量巨大,记录范围又广泛,作为古代天文档案间接遗存客观上为我们全面研究古代天学提供了更多的科学史料。
由于天学在中国古代以帝王禁学的面目出现,所以古代中国的天学文献中私人著述占的比例较小。有一些天学文献虽然以个人名义撰写,但也是奉了皇帝之命,即所谓“奉敕修造”。唐代瞿昙悉达奉敕编修的《开元占经》就是这样一部合法的天学著作。但《开元占经》能留传后世也是出于一次非常偶然的机缘。在唐以后的官方书目中已不见《开元占经》之名,直到明万历丁巳年(公元1617年)程明哲为一尊古佛重塑金身时,在大佛腹中发现了这一百二十卷《开元占经》。这部重要的星占著作得以保存下来,可谓非常侥幸。另外古代文人的笔记小说中也包含不少天学资料。明朝中叶以后,天学开禁,民间天文学家的有关天学著作成了私人天学文献中的最多的一部分。据笔者统计,其重要者约有三十几位五百余卷册。
从年代上来划分,以上包括直接遗存与间接遗存的天文档案遗存各有重点,大致为:秦汉以前主要从出土文物中获得;汉至明朝主要靠官方系统保存,如官史等;晚明、清代主要以档案馆中的档案原件与私家著述为主。
总而言之,由于中国古代天学的官方垄断性,给天文档案保存产生两方面的影响。首先,由于官方大量物力、人力的投入,保证了天学研究、天象记录的连续性,从而使天文档案得以以各种形式大量保存。其次,也正是因为天学在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是禁学,所以天文档案的保存渠道少而窄,缺少了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和流通,减少了被保存的机会。同时由于官方的集中保存,非常有可能由于战乱和火灾的原因而毁于一旦⑦。
明朝内阁大学士邱濬奏请建立皇史窚档案库时说:“经籍图书乃万年百世之事”,“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应“立为案卷,永远存照”。⑧这里邱濬所说的“立为案卷,永远存照”的意思,就是保存档案,以作历史的凭证。
中国古代天文档案遗存的科学文化价值,首先它是中国古代天学绵延几千年历史的真实凭证。因为天文档案不同于其他各种史料,它是当时当事者在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而并非嗣后为某种目的而撰写的著作或编制的材料。因此,中国古代天文档案遗存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天学高度发达的历史,是中国悠久文明历史的可靠的科学证据。另外,从中国古代天文档案本身的形体上来看,无论是殷商的甲骨文或是竹木制作的简牍文书,抑或是敦煌文书,它们从埋藏地下到被发掘出来为止,中间无人为的因素干扰,所以出土文物中的天文档案是研究古代中国天学的可靠资料。现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天文档案是官方仅保存的全面反映有清一代天文学活动的真实而系统的历史原件,其中不仅包括钦天监的原始观测记录“候簿”,而且还有大量钦天监进呈皇帝的题本。它们都有一定的格式,都盖有各执掌的印章和有关官员的签署。这些题奏都盖有皇帝的玉玺,有的还是皇帝亲笔书写的谕旨或亲自批阅的奏折。这些原始观测记录和题奏在处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历史标记,它确凿无疑地说明了天文档案遗存的凭证价值。例如:清朝《时宪书》中记载了每年中的节气,全国各地日出日落的时刻,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相配,推算出吉凶趋避。还专门记载了天体中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运行对人的影响等,是专门记载天文历法的系统资料。
天文档案不仅是历史的可靠凭证,而且是人们获取知识,促进历史进步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天文档案遗存中保存着中国古代各朝代循循相因的天学机构对天象持续的观察、完整的记录。它是当时天学家们知识的结晶,文化的历史积淀。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以作为今天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借鉴。例如:我们从天文档案遗存中保留的大量天学史料可知,中国古代天学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说明仅仅对中国古代历法或星占规则等进行孤立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要正确了解天学在中国古代的地位,必须放眼于古代史籍所载的大量具有科学社会学意义的天学史料(间接遗存中较多),这些史料同时也有助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古代知识系统的构成及其成长、运作等。
古代天文档案遗存中以下几方面具有科学社会学意义:一是天学机构的构成及其品级;二是天学与王权的关系;三是天学在古代中国文化各方面的特殊地位;四是天学家参与政治决策。
通过这些方面天文档案的遗存,可以发现古代中国天学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
天文档案遗存不仅保存有大量的知识,而且还记载有其他各种信息。例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档案,记载有中国最早的干支记日法。中国古代史籍《春秋·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的记载,是有关哈雷彗星回归的首次记录。中国古代盛唐时期,著名的“天竺三家”之一瞿昙悉达,其所撰写的《开元占经》集唐以前各家星占学说之大成,成为中国古代星占学最重要、最完备的资料库。它保存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恒星观测资料,特别是甘德、石申夫、巫咸三家星表,并记载了中国有史以来至八世纪所有历法的若干数据。
《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全面地搜集、考证了历代官史、明清实录、“十通”、地方志以及其他古籍中的天学观测记录,得到如下统计结果:日食记录一千六百余项;月食记录一千一百余项;月掩行星记录二百余项;新星及超新星记录一百余项;彗星记录一千余项;流星记录四千九百余项;流星雨记录四百余项;陨石记录三百余项;太阳黑子记录二百七十余项;极光记录三百余项;其他天象记录二百余项。
以上这些天象记录信息之丰富和完备,在世界天文学遗产中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对现代天文学而言,这些宝贵的历史信息是我们今天有关科研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天文档案遗存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制作材质多种多样,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持续悠久,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水平。特别是天文档案遗存中的出土文物,每一件都是珍贵的天学文献。例如,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当初是作为墓主陪葬品被深深埋藏于地下的,而一旦重见天日,则为研究先秦时期行星运动知识和行星星占学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敦煌卷子是保存至今的中国古代珍贵文献,其中有不少与天文有关,著名的《敦煌星图》就是一例。至于殷墟甲骨文中的天文记载,则为我们提供了历史非常久远的天学档案。从这些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它们不仅保存了中国各历史时期重要的天学史料,而且因其制作材质不同,形态各异,具有很高的文物收藏价值。又如明清档案中保存的大量天文档案,它们的内容系统完整,有着规范整肃的外形,精美的装潢,优质的纸墨、朱砂书写材料,反映了当时的文书制度和科技文化用品的较高工艺水平。明清天文档案遗存是中国丰富文化遗产中一批宝贵的财富。这些古老天文档案的存在便是我们文明古国的一种象征。
①《谈谈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上的天文图象》,《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②《中国的世界记录·科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③杨文衡:《中国科技史话》,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
④《唐会要》卷六十三。
⑤(清)光绪《湖南通志》第243卷,第39页。
⑥(清)康熙安徽《萧县志》第5卷,第9页。
⑦江晓原、钮卫星:《天学志》(陈美东主编:《中华文化通典·科学技术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⑧《明实录》第十二函,《孝宗弘治实录》卷六十三。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